一般来说,当我们去描述一个事物时,我们首先会对这个事物产生一个感知,继而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模糊的图像,最后生成对这个事物的语言描绘。这样看来,认识的产生先于语言,甚至会决定语言。
但是,语言有可能反过来对认识造成影响吗?语言与认识之间是一方决定另一方还是双方互为影响呢?
要进一步探寻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调动我们的视觉,以对颜色的感知为例,研究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有学者发现,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颜色词汇的产生极有可能遵循某种固定的顺序。每种语言首先都会先出现表示黑色和白色的词,或者表示最亮色和最暗色的词。随后出现在每种语言中的颜色词是红色,即血和酒的颜色。在红色之后,语言中出现了黄色,其后绿色(不过在一些语言中,形容绿色的词会先出现,随后才出现形容黄色的词)。最后出现在语言中的颜色是蓝色。
在古代文化中,无论是希腊、中国还是阿拉伯诸国没有“蓝色”这个词,《奥德赛》中描绘的海是“酒色”的;“天之苍苍,其正色邪”中“天”呈苍色;“春来江水绿如蓝”中“蓝” 则是一种染料,其所染的颜色则是青绿色;在日语中最早流传下来表示颜色的固有词也只有 “赤、黑、青、白、黄、茶”;古希伯来语《圣经》里对天堂的描述也没有提及天空是蓝色 的。目前来看,是古埃及文明创造了"蓝色"这个词,碰巧的是,他们也是现在发现的早期唯一可以生产蓝色染料的文明。

图一 埃及蓝——最早的人工合成颜料(ḫsbḏ‐ỉrjt)
蓝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颜色。几乎没有蓝色的动物,天蓝色的虹膜也是稀有的,蓝色的花朵则是后期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早期文化中,蓝色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缺失的位置。
那么,在人类文明产生形容蓝色的词汇之前,人类是否天生就能够看到并识别蓝色呢?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因为今人无从得知古人在描述酒色的大海和绿色的蜂蜜以及玄色的 天空时脑海中的思考过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古埃及人,他们都 与现代人有着相似的生理构造,因此也拥有相同的识别颜色的能力。
但是,如果缺乏相关词汇的形容,人们是否拥有识别这一事物的能力呢?
有学者曾前往非洲的纳米比亚地区调查过这个问题。在纳米比亚,他与当地的 Himba 部落进行了一项实验。由于这个部落使用的语言中没有 “蓝色 ”这个词,所以 Himba 部落的 人无法通过语言分辨蓝色和绿色。当他们看到一个有11个绿色方格和1个蓝色方格的圆圈时,他们大多无法分辨出哪个方格与其他方格不同。即便是一些能看出不同的人,他们在分辨过程中花的时间也会更长、犯的错误更多。而我们的语言中有“蓝色”一词,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蓝色方格。但是,Himba 部落的人对绿色种类的描述比我们用其他语言描述的还 要多。当看到一圈绿色方格中只有一个色调略有不同时,他们能立刻找出不同的那个。因此,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一个词来描述一种颜色、如果没有一种方法来识 别它的不同,我们就很难注意到它的独特之处,即使我们的眼睛接收到的颜色信息是一样的。

图二 Himba 部落成员参加蓝色与绿色识别测试

图三 你能辨认出其中的一块不同的绿色吗?

正确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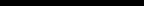
诚然,蓝色作为颜色的产生肯定早于“蓝色”这一概念的出现,因此,古人肯定很早就已经看到了蓝色,但是碍于抽象概念的滞后,他们意识不到这就是蓝色。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处理办法就是将蓝色与其他相近的颜色混为一谈,比如湘方言区和闽方言区的两种方言是不分蓝绿的,使用者会倾向于将蓝色统称为绿色。或者,他们缺少一位能够精准辨别蓝色并将其转化为语言表达的人。就如同现代人能够区分天蓝、宝蓝、深蓝,Himba 部落的人能够区分更多种类的绿一样。
因此,如果你看到了某种东西,却不能通过语言精准地形容它,那么它存在吗?真的存在所谓“黑白——红——黄——绿——蓝”的颜色产生规律吗?或者,当我们看见了一段文字,其描述一朵花的颜色之艳丽、姿态之极妍、花瓣之柔美,那我们会从这段文字中感受到或者联想到这朵花的香气和触感吗?
所以,究竟是我们生成的概念决定了语言的表达进而产生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我们的认识催生了语言表达并在脑海中得出抽象概念呢?语言,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工具,在决定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下限的同时是否画出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上限?
对于这些问题,相信每位读者心中有不同的答案,而随着不断求索,也会距真相越近。
引用:
[1]Bowmaker, J. K. (1998). Evolution of colour vision in vertebrates. Eye, 12(3b), 541.
[2]Finck, H. T.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 sense. Macmillan's Magazine, vol. XLI., pp. 125‐135
[3]Kay, P., & Kempton, W. (1984). What is the Sapir ‐ Whorf hypothe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1), 65‐79.[4]Lindsey, D. T., & Brown, A. M. (2002). Color naming and the phototoxic effects of sunlight on the ey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6), 506‐512.[5]Pitchford, N., & Biggam, C. P. (Eds.). (2006). Progress in Colour Studies: Volume II. Psychological aspect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6]Winawer, J., Witthoft, N., Frank, M. C., Wu, L., Wade, A. R., & Boroditsky, L. (2007). Russian blues reveal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19), 7780‐7785.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案:王思懿
审核:张放、焦辰、付阳、屈浩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