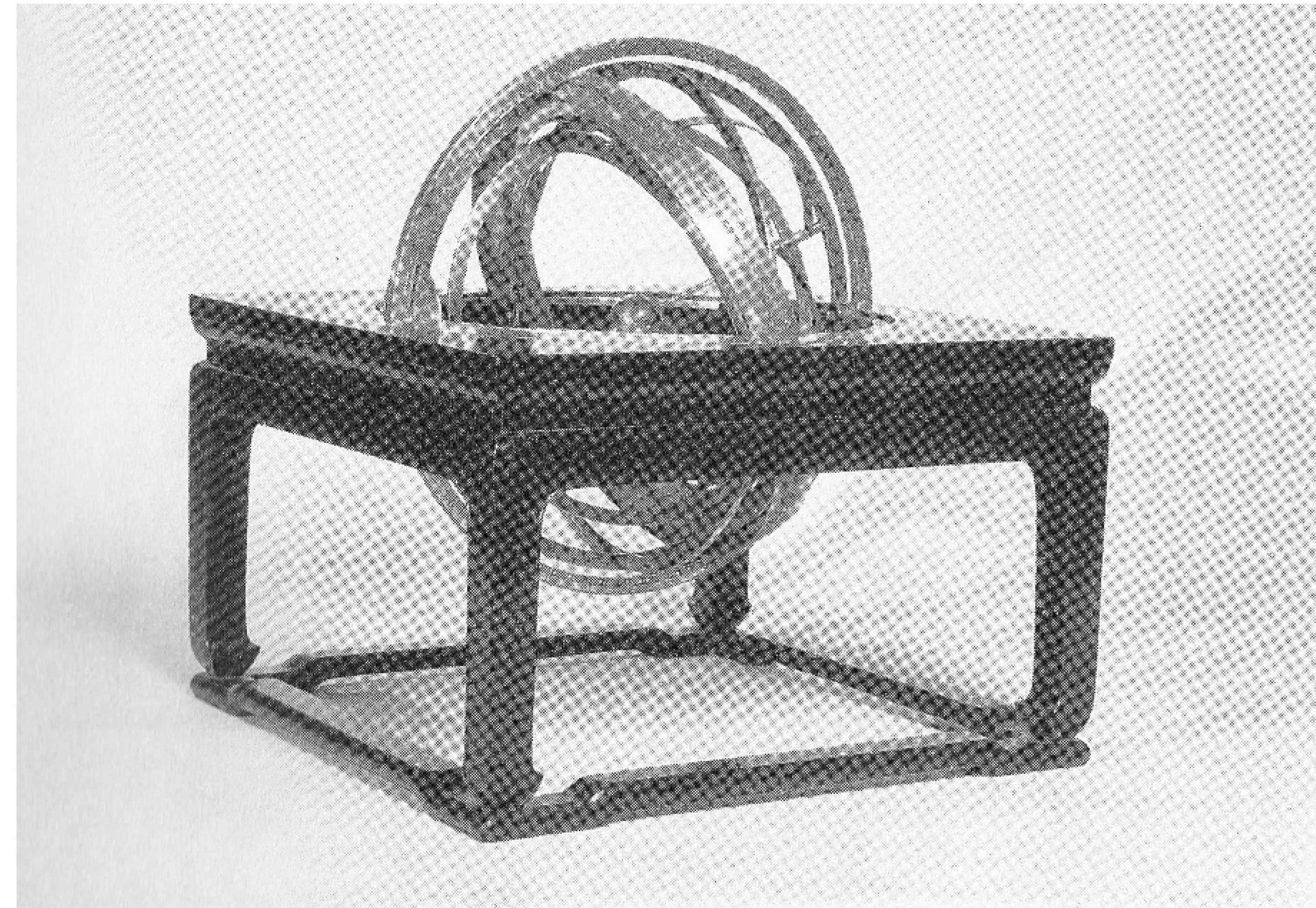
欧洲天文学在康熙年间从黑暗回归到光明。1668年和1669年,遵奉大清王朝康熙皇帝之命伴随我们一起在北京观象台进行天文观测的,有阁老们,还有很多在朝廷中地位显赫的高官。皇帝命令他们要成为我们每一次天文观测的目击者。一旦 (本文共 10623 字 , 11 张图 ) [阅读本文] >>
海量资源,尽在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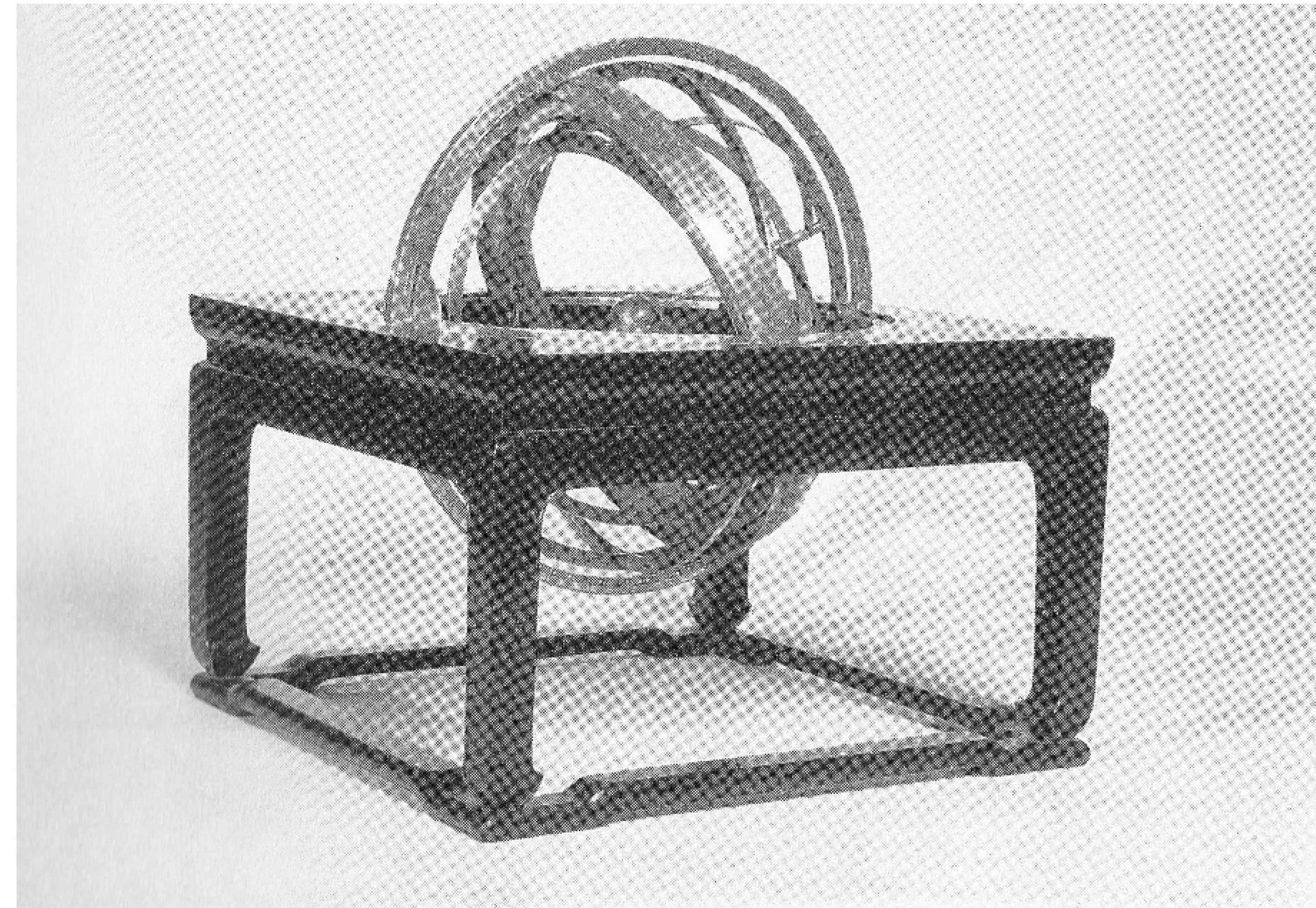
欧洲天文学在康熙年间从黑暗回归到光明。1668年和1669年,遵奉大清王朝康熙皇帝之命伴随我们一起在北京观象台进行天文观测的,有阁老们,还有很多在朝廷中地位显赫的高官。皇帝命令他们要成为我们每一次天文观测的目击者。一旦 (本文共 10623 字 , 11 张图 ) [阅读本文] >>